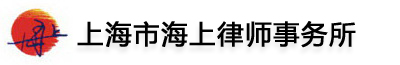案情介绍:
患儿为女性,出生时发现先天性左髋关节脱位,2岁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行闭合式复位治疗,术后恢复良好,能正常行走。后正常入学,平时步态平稳,看不出异常,也无其他异常。11岁即小学5年级时,因体育课剧烈运动后左髋疼痛,平时站立久后左髋也有疼痛伴轻度跛行,因而到黔南州中医院寻求进一步治疗。黔南中医院位于风景秀美的都匀市。
入院前四天,拍片提示:1、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术后半脱位;2、右股骨缺血性改变。
入院当日,医方为患儿实施了左股骨髁上骨牵引术。
牵引后第十天,患儿父母签署了《左先天性髋关节脱位Salter截骨术手术协议书》。签订协议书当天,做了Salter截骨术,取右侧髂骨植骨、左内收肌松解、左下股骨石膏外固定于外展30度。此手术的要点是改变骨盆的方位,使髋臼能与脱位之股骨头正常对位,从而恢复脱位之髋关节功能。
术后第17天,医方为患儿改行髋人字石膏外固定。4天后出院。
但出院后,患儿觉左髋部有硬物突起,左髋骶骨尾疼痛难忍,因而出院后一个月再次入院。
第二次入院体检发现:左髋前上嵴下方有骨性突起,轻压痛。复查片子提示:右髋下缘内侧移位,有少量骨痂生长。因而又于入院后两天签订《左股骨近端旋转截骨、左先髋Salter截骨术后调整手术协议》,并于当天行左股骨小粗隆旋转截骨术、Salter截骨术后钢板取出术、髋人字石膏外固定术。一个月后出院。此调整手术的目的与Salter截骨相同,即恢复髋臼与左股骨头之正常对位。
但第二次出院后,患儿未有任何好转,反而持续恶化:左腿无法站立,左髋疼痛难忍,骨盆严重倾斜,右髋取骨处也疼痛严重,由原来的正常行走、正常上学,变成无法行走,难以独立上学,即使家长送到学校,也不能坐在座位上,只能坐在教室旁边的轮椅上。
一年后患儿第三次住院。此次住院期间,拍片发现:左股骨头坏死。医方取出了左股骨截骨内固定钢板取出术,并作了内收肌松解术。
第三次出院后,患儿又先后到贵阳、北京继续治疗,但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左骨头坏死已不可逆,骨盆倾斜也不可逆,双髋疼痛仍日夜困扰患儿,坐卧不宁。后来在法庭上,对患儿现状,我如实作了如下描述:
1、髋关节功能障碍(股骨头坏死和骨盆倾斜),不能行走,已构成五级伤残;
2、双髋持续疼痛,坐卧不宁,睡眠质量严重影响,记忆力等学习能力严重下降;
3、生活难以自理,尤其无法独立大小便;因小便难以自理,不得不控制饮水,并自备矿泉水瓶排小便,即使处在教室也无法回避;又因更换卫生巾不方便,经期下体经常处于潮湿;以上种种使原告人格尊严受到直接伤害;
4、持久、深重的精神痛苦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医疗鉴定:
患儿父母无法接受如此严重的损害后果,怀疑医方手术存在问题,经多方咨询,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说法。患儿母亲虽为当地卫生局干部,便并不精通医疗诉讼的要点,于是在他人建议下,先不起诉,由黔南州卫生局委托黔南州医学会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患儿父母对本地医学会不信任,于是改由黔东南州医学会提供专家和场所进行鉴定,而由黔南州医学会出具医疗事故鉴定书。后黔南州医学会作出鉴定结论,分析极为简单:医方不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患儿目前损害无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事故。
患方当然不服,于是黔南州卫生局再次委托贵州省医学会进行鉴定。省医学会鉴定认为:1、医方为患儿行三次手术治疗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均有手术指征,治疗过程中未违反医疗规程。2、患儿目前出现的股骨头坏死原因有:(1)股骨头坏死是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可能出现的后果;(2)手术可以干扰血运,影响股骨头血液循环(但医方未违反规定)。最终结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法院审判:
拿到两级医学会均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之后,患儿父母仍无法放弃,在律师建议下,决定起诉到法院一试运气。结果可以想见,很快都匀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根据两级医学会的鉴定结论, 被告无医疗过失,不予支持原告之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患儿父母立即上诉。此时想到更换律师,于是千里迢迢到上海找我。
我问他们上诉理由是什么?他们回答,至少有两点:
第一,被告篡改了入院诊断。原告在医疗鉴定前并未复印病历资料,只是在医疗事故鉴定过程中,才从医学会复印到病历,这时才发现医院篡改了入院诊断,即将原来的“左股骨缺血改变”改为“双侧股骨缺血改变”,篡改的方法是将“左”字用双横线删去,然后添上“双侧”二字。事实是,根据入院时的拍片报告,患者实为右股骨缺血改变,左侧并未出现缺血改变。另外,患儿手术后出现的股骨头坏死是左侧,而不是右侧。因此即使右侧股骨有缺血改变,也与本案争议损害后果无关。篡改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证明患儿在术前已有左侧股骨缺血改变,减轻医方责任。这一点在后来的重审中法院予以了查明。
第二,医学会擅自拆封已经封存的病历,不能排除医院据此拿到已经封存的病历并伪造之。原来患方在医学会复印后又对原始病历进行了封存,后来患者母亲在与医学会的一次交涉过程中(此时尚未鉴定听证)发现医学会擅自启封了患患共同封存的原始病历。
至于医方在salter截骨术中的具体医疗技术过失,患儿父母限于医学知识,无法得知,也无法提出。
我分析道:
第一,鉴定专家对股骨是否存在缺血改变的判断依据是原始片子,而不是书面的入院诊断。因此虽然医方篡改入院诊断存在过错,但不足以影响鉴定结论,仅凭此点,上诉法院无法推翻两级鉴定结论;
第二,医学会擅自启封医患双方共同封存的病历确实存在程序上的严重错误,但是经比对你方在启封前复印到的病历与医院提交的病历原件,二者是完全一致,因此不能证明医学会的擅自启封导致医院伪造了病历,除非你们能够直接证明你们手中复印到的病历在启封之前早已进行了伪造,但目前看,你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故仅凭医学会擅自启封病历而说服上诉法院推翻鉴定结论,难度极大。
第三,我分析了你们之前交过来的病历和片子,也查了不少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手术诊疗规范,认为医院可能存在以下过失:1、违反了手术年龄指征,salter截骨术的适宜年龄是6岁前儿童,而本例患儿已达11岁;2、截骨术前未进行拍片复查,不能证明股骨头与髋臼已达到同心复位;3、截骨术后第17天才进行髋人字石膏固定,违反诊疗规范;4、从术后片子可以看出,固定螺钉已有脱出,说明固定不牢等等。我进一步补充,这些过失影响股骨头血运,与股骨头坏死有关。因此本案只有从医学技术专业本身入手才有翻盘希望,仅在病历伪造上作文章于事无补。
最后,我说,你们已经上诉,上诉能够改判的唯一可能是申请重新鉴定,通过重新鉴定推翻之前的两级医学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而且重新鉴定,不要选择中华医学会,应当选择医学会之外的其他社会鉴定机构。
关于向上诉法院申请重新鉴定,我特别强调了法律上的难点,因为你们在一审中并未申请到医学会之外的机构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而按我国法院审级,二审法院通常不接受新的鉴定申请,不接受新的证据,因此你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决心说服二审法院,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为他们书写了重新鉴定申请书,重点阐述了法律上的理由,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的通知(注:此案发生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前),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分为两种,一是医疗事故赔偿纠纷,一是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本案诉前仅仅进行了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只能证明不存在构成医疗事故的过失,但不能证明不存在医疗事故之外的医疗过失,因此关于上诉人到医学会之外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失司法鉴定的申请应予准许。
对于法院是否准许这个重新鉴定申请,我也吃不准。因为在有些法院比如上海,就认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只有一个案由即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医学会是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定机构,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就表明这个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不符合侵权责任成立的全部要件,支持诉讼请求的证据不存在,也不存在再行委托其他机构进行鉴定的可能。当然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生效后,所有医疗侵权的案由都是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不存在医疗事故这个法律上的概念了,但鉴定中的二元制仍然存在,即仍然存在医学会和医学会之外两类鉴定机构。而且即使在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后,其些医学会仍然将医疗技术鉴定称为医疗事故鉴定,其鉴定程序和鉴定结论的书写,仍然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
大约两个月之后,我接到当事人从贵州打来的电话,黔南州中级法院将案件发回都匀市人民法院重审,发回理由就是应当允许上诉人到医学会之外的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原审事实不清。这是一个初步胜利,当然我也知道能够得到这个结果,患儿父母付出了极大努力。
发回重审后,都匀市人民法院通过黔南州中级法院委托了北京的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
到北京参加鉴定听证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患儿,一个13岁的女孩,坐在轮椅上,很阳光。可以看出没有受到长年诉讼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对孩子保护得较好,没有将诉讼中的委屈、愤怒、压抑感染给孩子。但是病痛的折磨,孩子只能自己忍受。
鉴定那天还发生一个小插曲。早餐时,我们在餐厅巧遇了都匀市人民法院前来北京参与本案鉴定听证的两名法官,两人都穿着黔地苗族人特有的民族服装,就象每年两会期间进京参会的少数民族代表。我们对她们远远点头笑了一下,但没有谈话,更没有上去抢着买单,呵呵。
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全部由骨科医生组成,没有法医参加。这与其他社会医疗损害鉴定机构不同,其他机构多数由法医主持鉴定,虽然涉及医学专业问题有时会邀请临床医生参加鉴定,但临床医生起的作用主要是提供鉴定咨询意见,其并不在鉴定书上签名,也不承担鉴定责任。而中国科协的临床医师鉴定人员具有独立的鉴定人资质,在鉴定书上签名,对鉴定结论直接负责。
鉴定现场,专家对医方问得非常犀利,好多问题他们难以回答。最后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专家基本上采纳了我陈述的观点,鉴定结论认为医方存在以下缺陷:
1、手术指征不明确,salter截骨术多适用于6岁前儿童,患儿手术时已11岁,医方未采取相应的特殊措施;
2、医方手术前未能将髋关节牵引达到同心复位,致手术失败;
3、salter截骨术时嵌入植骨、钢板固定不牢固致术后螺钉脱出,截骨术失败;
4、未在麻醉中止前行髋人字石膏固定;二次手术穿入股骨头螺钉位置不合理,影响股骨头血运。
鉴定结论认为,上述缺陷使被鉴定人股骨头坏死概率增加,是其髋关节障碍的次要原因。但股骨头无菌坏死系股骨近端旋转截骨的常见并发症,被鉴定人目前髋关节功能障碍主要系自身疾病所致,
但患儿父母对医方仅承担次要责任不满,认为如果没有医方的错误手术,根本不可能出现左侧股骨头坏死,因而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对此,根据我的经验,再通过鉴定程序改变责任比例恐怕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法庭辩论,因为从根本说,因果关系与参与度属于法律问题,应由法庭通过过错、后果、因果理论、逻辑等进行独立的法律判断。
科协鉴定后,法院又陆续委托贵州省内的鉴定机构对伤残等级、护理、营养、后续治疗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其中伤残等级包括双髋功能障碍和左股骨头坏死构成五级伤残,护理等级为三级护理依赖。
开庭那天,气氛非常紧张,旁听席坐满了人,数名法警站在患方当事人一边,当然不是保护,而是防止当事人现场发作。好在最终庭审顺利进行,双方未在法庭内起激烈冲突。
一审判决,没有采信黔南州医学会和贵州省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是按照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的结论判决医方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其中护理费按一人护理的0.3倍承担,加上残疾赔偿金、已有损失、营养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等共计赔偿30万元。
一审判决后,患方不服再提上诉。上诉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中级法院改判49%的赔偿比例,护理费改判按1人护理计算,精神损害由2万增加到6万,总的赔偿额改判支持50余万元。
记得最后一次开庭傍晚,我与当事人坐在黔南州首府都匀的剑江河畔,两岸莺语流花,青山耸翠,河中不时有渔船划过,捕鱼唱晚。如此美丽的地方,一旦遇到法律纠纷,则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模一样,渊深黑暗,深不见底。而本案作为医疗诉讼,我的当事人,竟然还是卫生局的职工,如此际遇,不胜唏嘘。
案件分析:
本着一案一问题的讨论原则,本案例也仅讨论一个问题,虽然本案可能涵盖了医疗诉讼中的所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医疗诉讼中的二元制鉴定:医学会鉴定与医学会之外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二元制鉴定问题也很大,仅说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本案关于医疗过错共进行了三次鉴定,前两次是医学会鉴定,地市级一次,省级一次,结论均是医院不存在过错,不构成医疗事故;最后一次是社会司法鉴定机构也就是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医院存在医疗过错。
这三次鉴定的共同之处,鉴定人员都是骨科医生,具备本专业的鉴定知识,因而不存在目前医学界经常反对的社会鉴定机构是法医鉴定,鉴定人员是法医,法医根本不懂临床医学,对诊疗行为进行司法鉴定是胡乱鉴定、是超越知识范围的鉴定等情形。
同是临床医生作为鉴定专家,为何在不同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就不同呢?难道鉴定也有淮橘为枳?医学会的鉴定专家到了其他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就可能变得更加公正了?
我认为在医疗损害鉴定领域,确实存在淮橘为枳。这个淮,其实就是鉴定人的身份。医学会的鉴定机构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而组建,不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约束,其业务领导是卫生行政部门而非司法局,其鉴定人身份系卫生系统推举任命而不在法院登记在册,其在医学会的鉴定身份不是司法鉴定人,不是个人身份,而是以某个医院的专科医生身份参与鉴定,其对鉴定结论不用承担个人责任,其也不必因鉴定结论而对法院和法律负责,其负责的对象是所在医院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换句话说,鉴定人在医学会进行鉴定,更多的是一种可以印在名片上的学术荣誉,而不是法律上的一种职责和义务。所以,医学会鉴定专家的医疗损害(以前称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鉴定结论虽然被法院直接拿来当证据使用,但其整个鉴定程序却是医疗系统的内部操作,与法律和法院无缘。
但同样是临床医生,如果是作为鉴定人参加医学会之外鉴定机构的鉴定,其身份就大为不同,因为医学会之外的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必须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那么,一、他必须取得司法鉴定人资质,这个资质由司法行政部门颁发;二、其所在鉴定机构必须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该临床医生及所在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想作为证据进入法庭,还应当取得法院的许可,也就是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均应在法院登记造册。四、有了上述身份的转变,此时的这位临床医生就不再是某个医院的主任或者专科医生,而是一个独立司法鉴定人,其参加鉴定不再是代表医院而是代表个人,其参加鉴定也不再是一种可以印在名片上的学术荣誉而是一个专业人士的法律义务和职责,其鉴定结论除了对法律和法院负责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其参与鉴定可以取得理所应当的报酬。
所以,同样是医疗过错的技术鉴定,医学会的鉴定与医学会之外鉴定机构的鉴定,竟有如此大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临床医生,分别以不同身份参加这两种鉴定时,其结论都可能淮橘为枳,何况是不同的医生参与这两种鉴定。